近几年流行一种“合伙人”的机制,包像海底捞、西贝、永辉超市这样的大型餐饮及零售企业都导入了“合伙人”机制。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机制,本质上还是为了激发团队活力,使团队能够与组织像血肉一样地紧紧相连。
1.“合伙人”机制产生的背景
在企业传统的生产关系中,股东、管理层、员工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指令关系和分配关系。企业管理决策从上向下级传达,但被动接受指令的下级因理解能力、个人利益和主观动力等原因会导致执行力度层层递减,最终导致经营效率的损失。企业经营成果的分配完全由上级决定,并通过固定薪酬、绩效考核等一系列手段进行绩效评价和发放,下级同样处于被动消极的状态。
在合伙人思想指导下,员工不再是单纯的劳动力出卖者,而是成了自己的主人。新的生产关系极大提升了人才的内生动力,从根本上改变了人力资源利用效率。由于角色的转变,上下级之间单向命令式的被动管理所带来的消极作用被基本消除,各方开始主动提高工作配合、速度和质量,管理成本开始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员工自己的付出,决定自己的收入,付出回报更紧密,具有更高的激励性,同样为员工开辟了一条收入通道。
2.“合伙人”机制的内容
从目前各类企业实施的“合伙人”机制来看,主要分为两种:事业合伙人和业务合伙人。
(1)事业合伙人
事业合伙人即常见的虚拟股份或项目跟投,员工出资认购公司虚拟股份,共同经营、共享利润、共担风险,但并不涉及法人主体或工商注册信息变更。其中又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公司拿出一项业务、产品、项目、区域(单店)等可独立核算的经营体与参与该经营体运营的员工共同投资、共享利润、共担投资风险,如万科的项目跟投、很多连锁企业的单店员工入股;第二类是公司不区分不同业务/项目/区域,其虚拟股份对应整体经营盈利情况,全体合伙人出资认购公司整体的虚拟股份,并根据公司整体盈利状况进行分红、承担风险,如华为的内部员工持股计划。
(2)业务合伙人
业务合伙人是基于业务层面而非公司层面,主要与公司的某一项具体业务有关,也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经营团队独立自主进行业务开拓与执行,享受团队经营所得的利润,这是合伙人制最早的形态,常见于智力服务机构,如管理咨询、会计师事务、律师事务所、投资银行等轻资产运作的机构;第二类则类似于承包制的演化,即在公司确定的业绩、利润基础之上,由经营团队通过努力实现的增值部分进行利润共享,适用于非轻资产运作但员工对业绩/利润起到较大作用、员工经济实力不足以进行资金跟投的企业,更多应用于基层员工的合伙人制改造,如永辉超市推行的一线员工合伙人制,不涉及法人主体及股份身份事宜。
相对而言,业务“合伙人”机制更适合经销商采用,对此可以借鉴一些厂家的实施方式。以海底捞旗下的颐海国际为例,其2018年导入的“合伙人”机制产生了良好的效果:销售人员以其负责的经销商作为业务单元,给其充分的费用使用权利,同时考核标准从已有的“完成收入”改为以“业务单元的净利润”,以利润的 5%为销售业务人员核算奖金,不设上限。“合伙人”机制的实施,充分激发了销售人员主观能动性,使企业员工达成目标和利益的一致,大幅提高了单位费用的使用效率,销售团队积极性也得到充分激发,同时规避了目标责任制中为了降低未来收入指标而刻意压低今年销售的短期行为。在新的激励机制下,相当数量的合伙人月收入3万元以上,2018年颐海国际的第三方收入(指通过经销商拓展市场)大幅提升106.1%,远高于营销费用增速,人均创收从2017年的18万元/月翻倍至2018年的36万元/月。颐海国际的改革成效斐然,其2019年的营业额已经高达42.83亿元,同比增长59.7%,净利润为7.95亿元,同比增长也达到了59.71%,远远超过了天味、红九九等原来的领先品牌,成了火锅调料行业的第一品牌。
据笔者了解,目前一些营业规模较大的经销商已经准备导入“合伙人”机制,应该说这是经销商不断追求进步的良好表现,值得肯定。不过,笔者在此要提醒的是,经销商对此不应赶时髦,而要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恰当的员工激励方式。“合伙人”机制的本质就是“利润分成”,与前面所述的做法并没有本质的区别,都能很好地激励业务团队的积极性,只是叫法不同而已。“合伙人”机制只是薪酬激励方式的一种,并不能代替正常的薪酬体系,要发挥出作用也要建立在一定的管理基础之上,不能将其孤立出来看待。“合伙人”机制适合规模大的厂商,对大多数的经销商来说,更重要的先将一套相对完整的薪酬体系建立起来,把原先零散、粗放、随意的激励方式逐步变得规范,同时使团队意识和行为得到转变。然后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张,在各种基础条件都已经夯实的前提下,再逐步导入“合伙人”机制,就能够发挥较好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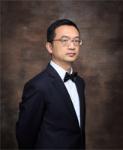 张戟
张戟

